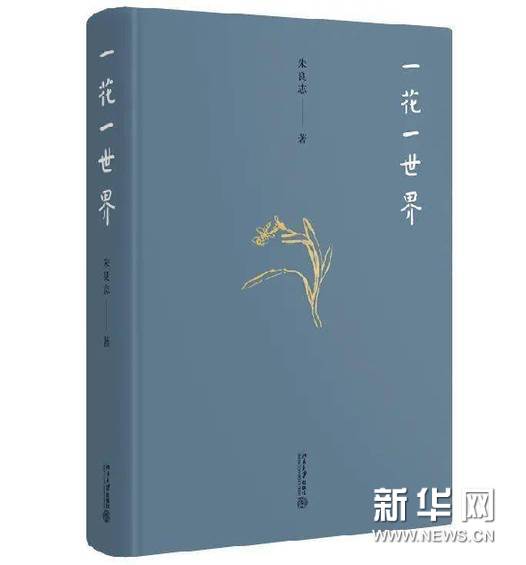
推荐理由:“天雨流芳”是纳西语,意为“读书去吧”。新华网文化频道【天雨流芳】栏目将陆续推出当代名家名作系列品读,让心灵如同沐浴天雨一样得到知识和智慧的滋养,一瓣心香,让灵魂绽放出生命的清香。国庆中秋双节到来之际,我们奔波不安的灵魂需要得到诗意的栖居。所谓:“落花无言,人淡如菊。书之岁华,其曰可读。”
古人云:“净几明窗,一轴画,一囊琴,一只鹤,一瓯茶,一炉香,一部法帖;小园香径,几丛花,几群鸟,几区亭,几拳石,几池水,几片闲云……”
推荐大家静心品读北大朱良志先生的新书《一花一世界》。本书讨论传统艺术哲学中“一朵小花的意义”。佛家讲“一花一世界,一草一天国”,意在说一花、一草这样的“小物”也有它自己存在的逻辑和价值,本身就是一个完满的价值和意义世界,是一种“大全”,没有缺憾,不需要补充。恰如“白日不到处,青春恰自来。苔花如米小,也学牡丹开。”
本书即以人类的艺术生活为切入点,来说人生命存在的价值,也是在讲一种回到世界、归复本真的智慧。上篇主要是一些观念性的讨论,如“无量的世界”“懒写名山照”“大成若缺”“让世界敞亮”“由青山白云去说”“德将为汝美”“无上清凉界”,下篇涉及一些具体的艺术家,如陶渊明、王维、白居易、苏轼、倪瓒、石涛、黄宾虹等,理论和个案相结合,共同呈现了传统艺术哲学的这一重要面向,富有理论深度和穿透力。

一
元代艺术家倪瓒(号云林,1301—1374)题兰画诗写道:“兰生幽谷中,倒影还自照。无人作妍暖,春风发微笑。”一朵野花,开在幽深的山谷,没有名贵的身份,无人问津,没人觉得她美,也没人爱她,给她温暖,她倒影自照,照样自在开放——她的微笑在春风中荡漾。
这首诗寓含一个道理:一朵野花,也是一个有意义的世界,一个圆满宇宙。
从人知识的角度看,野花是微不足道的,并不具有意义。但野花可不这样“看”,她并不觉得自己生在闭塞的地方,也不觉得自己形象卑微,有所缺憾。野花“并不觉得”,其实是无法觉得。而人是有“法”觉得的。在人的“法”的眼光中,有热闹的街市,有煊赫的通衢,也有人迹罕至的乡野,人们给它们分出彼此,分出高下。人们眼中的花,有名贵的,有低下的,有万般宠爱的,有弃而不顾的。像山野中那些不知名的小花,人们常常以为其卑微而怜惜之。
“任真无所先”(陶渊明《连雨独饮》),中国古代有一种思想智慧,要归复人的真性,破这先在的“法”。大和小,多和少,煊赫和卑微,高贵和低下,晦暗和灿烂,是人知识眼光打量下的分别,庄子将这称为“以人为量”。科学的前行,文明的推进,的确需要这样的眼光。但是,并不代表这样的眼光是当然的。在人为世界立法的眼光中,人们以知识征服世界,以秩序分割世界,将世界当作对象,似乎不属于世界。人站在世界的对岸看世界,给它确定意义,这样的世界是被知识、情感等过滤过的,并不是真实的世界。其实,人本来就是世界中的存在,不能总是在世界的对岸打量它。当由世界的对岸回到世界,回到生命的故园时,你随白云轻起,共山花烂漫,以世界的眼光看世界,“任真”——依世界本来面目而呈现,即庄子所说的“以物为量”,这时一朵小花便有了意义——不是以人的观念决定了的意义。

本书讨论的传统艺术哲学中“一朵小花的意义”,是一种回到世界、归复本真的智慧。在森然的理性天地里,艺术家、诗人等热衷于去发现“一朵小花的意义”,是因为这微小存在的意义往往被忽略,甚或被剥夺。历史的丛林,人世的江湖,常常碾压着微小存在的梦。其实,恒河沙数,宇宙中每一个存在都可以说是微小的,短暂而脆弱的人生更是如此。一朵小花意义的顿悟,其核心是强调,生命本身就是一种权利,知识和秩序是人的创造,但不能成为霸凌的工具,人不能将世界的一切置于知识、欲念的统治之下,或者居高临下地“爱”它、悲天悯人地“怜”它,或者无情地卑视它。一朵小花也有存在的逻辑和价值,并不因外在的评价和情感投射获得存在的理由。
面对存在意义的坠落,先秦的老庄哲学等就曾有过关注。“感时花溅泪,恨别鸟惊心”(杜甫《春望》),诗人和艺术家毕竟是敏感的生存类别,我们看到,中国传统艺术发展中对此问题的重视,由开始的细微之声,唐宋以还,渐汇成深沉阔大之音。这直接影响着中国千余年来的艺术创造,甚至人们的生活方式。
在中国传统艺术的创造中,潜藏着如潘洛夫斯基所说人类悲壮的“自我约束原则”这一深沉的人文精神。接触唐宋以来的艺术事实就会发现,诗人、艺术家常在做“损”的功夫,形式上多做“减”法、“简”法。一池碎、满目枯荷的意象世界,往往传递的是这深沉的生命关怀。诗人、艺术家钟情枯木寒林之相,刻意渲染荒寒寂寞气氛,躲到无上清凉世界,去冷却心中的躁动,恰恰表现的是殷切的生命关怀意识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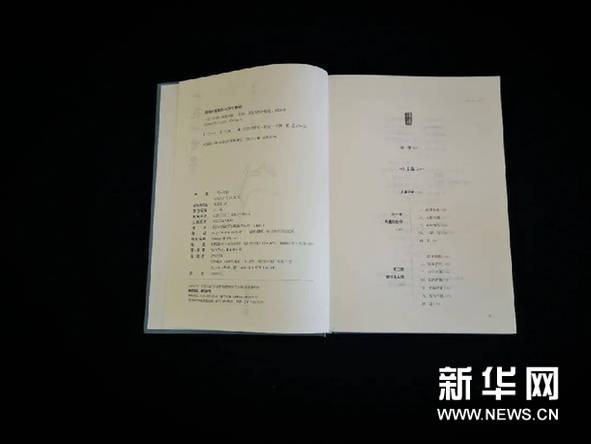
苏轼说:“以爱,故坏;以舍,故常在。”(《东坡志林》)一个“舍”字,可以说是唐宋以来中国艺术哲学的灵魂。倪云林兰生幽谷的喻象就突出这“舍”的精神:在空旷无垠的山谷中,一朵微小而孱弱的兰花,其量上的“舍”,几近于无。中国艺术家要于此“舍”中,觑生命本相。“舍”,是为了挣脱羁縻,纠正人类缘由知识所产生的欲望扩张,那无尽的“爱”——占有的愿望,追寻在“人文”名义下被剥夺的存在权利。艺术家更在“舍”中,传递出人对世界的宽容和责任,维护人作为生命存在的基本尊严,在超越先在的“人文”附加过程中,建立更切近人生命的真正的人文世界。
二
说一朵小花的意义,不是说一个客观对象的意义,而是对存在意义的“发现”。意义是在直接生命体验中产生的,不由先在态度所支配。石涛以“法自画生”(《画语录了法章》)四字概括这种精神。法,“只在临时间定”(《大涤子题画诗跋》),它是即成的,当下的,直接的,自我的,也是鲜活的。这种哲学推重生命的鲜活感受,是“活泼泼”的,而不是为完成某种预先被确定的事实,去敷衍其事。在这种观念看来,从属性的劳作,终究是无意义的呻吟;应到自己真性中汲水,这里有永不枯竭的生命之泉。如唐代诗人寒山所说:“寻究无源水,源穷水不穷。”不要让外在的道、高飘的理、妙用无方的神等终极价值来支配你,没有外在的“源头”,直面生命体验的真实,才能发现生命的活水。道,在自我行走的道路上;神,在心灵的体验里;理,就在生命展开的逻辑中。
这里所说的当下体验,是在无遮蔽状态下亲近世界、与世界融通一体的存在方式,而非冥思或源于直觉的认识能力。瞬间妙悟,其实就是让世界自在兴现的智慧。唐代哲学家李翱是一位儒家学者,对佛学有兴趣,而药山惟俨的大名在当时朗如日月。一次,他去拜访药山。见药山时,开口便问:“如何是道?”药山并未直接回答,当时他坐在门前,门前置一案,案上放着一杯水,还有几函没有打开的经书,他向上指指天,向下指指案上的水,说:“云在天,水在瓶。”李翱豁然有悟,写了两首诗,第一首道:“练得身形似鹤形,千株松下两函经。我来问道无余说,云在青天水在瓶。”道在不问,佛不在求,不在读经,不在静修,只要放下心来,将系缚自己的绳索解开,与世界融通一体,处处都有佛,时时都是悟。云在青天水在瓶,这是一种任由世界自在兴现的哲学。唐宋以来的艺术,在很大程度上,就是这种自在兴现生命体验的记录。

说一朵小花的意义,也是在说平等的生命智慧。存在的意义是由平等铸就的。平等,不是知识的平衡、秩序的斟酌,而是对秩序与知识的超越。“木末芙蓉花,山中发红萼。涧户寂无人,纷纷开且落”(王维《辛夷坞》),山中自开自落的花儿,也是真实的,有其不待给予、不容卑视的独立存在意义。生命是平等的,我们不能因为文明推进,有太多的“文明”手段,有复杂的知识分别,只知道证明自己的至尊高贵,精英们忙着回护自己的地盘,就忘记了别的存在的意义。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,一朵小花也有她的无上尊严。我们以掠夺别的存在获得自我存在到了得心应手之时,记得一朵小花也有她的存在权利,或许有好处,它让我们离真实世界不会太远。传统艺术常常以寂寞的形式,去记录远离羁縻的畅然、发现意义的欣喜。艺术家在萧瑟、质朴、单纯的境界营造中,玩味“小”的意义。这不是一声无奈的叹息,这里有金翅擘海的勇猛。看倪云林的数株寒林昂首于高莽云天的清影,就会有这种感觉。唐宋以来艺术传统中“贵族意识”的弱化,与此一哲学密切相关。
“一花一世界,一草一天国”,其根本旨意在生命的安顿,它是一个价值世界。隋唐以来哲学中说“小”,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为了说“大”,说“圆满”,说太不圆满人生中的“圆满俱足”,说心灵的高蹈与回环,所谓“月印万川,处处皆圆”。听哲学家说“一月普现一切水,一切水月一月摄”(永嘉玄觉《证道歌》),其中就暗含这个道理。当下直接的体验是一种“大全”智慧,没有缺憾,不需要补充。圆满的降临,取决于人是否有生命的“定力”,是否有生命的“俯仰自得”的功夫。韦应物《滁州西涧》咏我家乡的一条小河,是一首童叟皆知的诗:“独怜幽草涧边生,上有黄鹂深树鸣。春潮带雨晚来急,野渡无人舟自横。”所吟咏的就是这俯仰自得的圆满智慧。狂草大家张旭以鲍照《芜城赋》中“孤蓬自振,惊沙坐飞”为毕生追求的最高境界,也是此理。正像陶渊明所说,“寒华徒自荣”(《九日闲居》),一朵在萧瑟秋风下独自绽放的淡然的菊,无所求,不畏凄寒,不以荣为荣,自有璀璨的生命光芒,有难以言传的美。这个看起来微小的“一”,就是圆满俱足的“一切”。说一朵小花是一个大全世界,是在砥砺生命信心,不仰望外在“态度”的变化,要在归复内在心灵的平宁,心安即归程。
传统艺术哲学将这独特的生命绎思凝固在四个字中:小中现大。大,是价值的实现。
三
这就是我近日草成、奉献给读者的新作所要研究的中心问题,它也是二十多年前就引起我研究兴趣的问题。我在这个世纪初出版的《曲院风荷》中有“微花”一讲,涉及此问题;此后出版的《中国美学十五讲》中有“以小见大”一讲,谈到此问题;稍后做石涛研究,剖析他的“一画”时,触及此问题;《南画十六观》讨论文人画“真性”问题,也不离这个关键问题。这是我最想写的一本书,也是我深感学力不逮、很难完成的一本书。它是我关于艺术的见解,也是自身关于生命存在的切身体会。现在忐忑地将这部不成熟的作品呈现在您面前,希望能得到您的指正和帮助。

本书所讨论的问题,在中国传统艺术哲学中具有不可忽视的位置。它不是一本书、一个理论家、一个时代所拥有的思想,而是中国诗人、艺术家和智者泛舟于知识瀚海时,对生命意义的追问。艺术是心灵的轻语,生命存在的价值是其永不消歇的话题。它是诗、书、画、乐、戏曲、建筑、园林乃至篆刻、盆景等创造背后所潜藏的问题,是诗家吟咏的主题,也是很多画家要表达的秘意。造园家做一个小品,在纳千顷之浩荡、收四时之烂漫中,有此驻思。篆刻家在方寸天地腾挪时,亦萦绕此意。拘谨的文徵明说:“我之斋堂,每于印上起造。”他的烂漫思虑中,包含这一思想。既是词人也是词学理论家的张炎(1248—约1320),咏着秋风,说:“只有一枝梧叶,不知多少秋声。”(《清平乐候蛩凄断》)优雅言辞中,也氤氲此一哲思。高才的苏东坡评画说:“谁言一点红,解寄无边春。”(《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》其一)正是由此哲学萌发出的思考。恒河沙数,生命是微小而脆弱的,传统艺术哲学小中现大的智慧,通过妙用恒沙的追踪,来展现人的存在价值。总之,本书说一朵小花的意义,乃是以人类的艺术生活为切入点,来说人生命存在的价值。

作者简介

朱良志,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,北大博雅讲席教授。研究中国美学三十余年,长于中国哲学与艺术关系的分析,从中剔发中国人的人生智慧。其独特的思想观念和表达方法,受到当代学界和读书界的关注。
出版《南画十六观》《真水无香》《中国美学十五讲》等著作,曾获中国出版政府奖、中华优秀出版物奖、“中国好书”奖、中国美术奖、中国文联文艺评论著作特等奖、教育部高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等。


